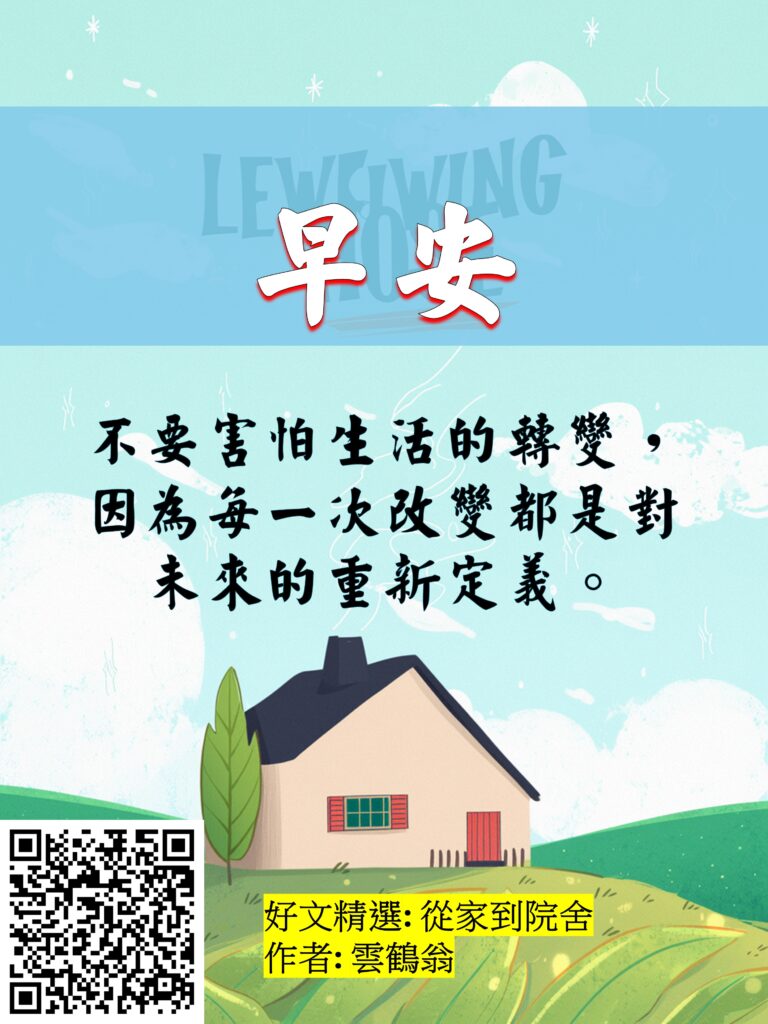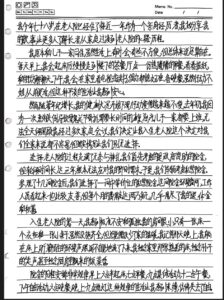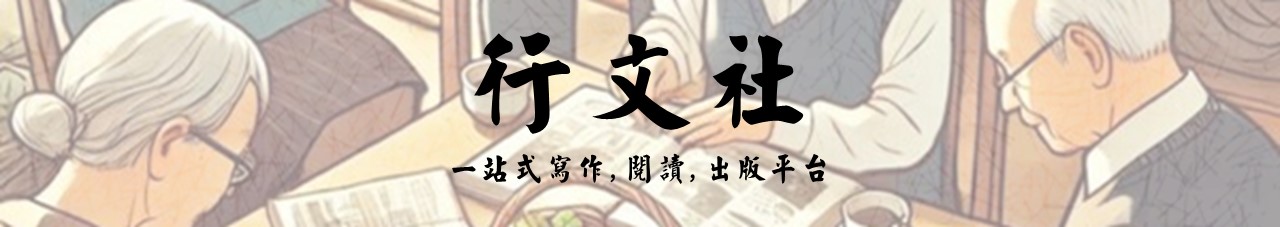
從家到院舍
雲鶴翁
我今年七十八歲,在老人院已經住了將近一年。作為一個親身經歷者,我想分享我的故事,讓更多人了解長者從家庭過渡到老人院的心路歷程。
我原本和兒子一家同住,雖然生活上有時會有些不方便,但總體來說還算自在。每天早上,我會起床後慢慢走到樓下的茶餐廳,點一份熱騰騰的早餐,看看報紙,和街坊聊聊天。下午,我會在家裡看電視或讀書,偶爾幫媳婦準備晚餐。雖然行動不如從前靈活,但這種平淡的生活讓我感到安心。
然而,隨著年紀增長,我的健康狀況開始下滑,行動變得越來越不便。去年初,我因為一次意外跌倒,導致髖關節骨折,需要長時間的康復治療。兒子一家都要上班,無法全天候照顧我,經過多次家庭會議,我們決定讓我入住老人院。這個決定對我們全家來說都不容易,但現實情況讓我們別無選擇。
選擇老人院的過程充滿了無奈與掙扎。我們首先考慮的是政府資助的院舍,但輪候時間長達三年,根本無法應對我的即時需求。於是,我們轉而考慮私營院舍。參觀了十幾間院舍後,我們選擇了一間中等價位的私營院舍。這間院舍環境尚可,工作人員看起來也比較友善,但每個月的費用高達兩萬多元,幾乎用盡了我的退休金和積蓄。
入住老人院的第一天,我感到極度不安和孤獨。我的房間很小,只有一張床、一個衣櫃和一張小桌子。雖然設施齊全,但總覺得缺少了家的溫暖。我記得那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聽著陌生的環境聲,眼淚不自覺地流了下來。我想念家裡那張熟悉的床,想念孫子的笑聲,甚至想念廚房裡飄來的飯菜香。
院舍的日程安排非常規律,早上六點半起床,七點早餐,九點集體活動,十二點午餐,下午自由活動,六點晚餐,晚上九點熄燈。這種規律的生活讓我感到束縛,彷彿失去了自由。早餐通常是粥和饅頭,雖然營養均衡,但味道平淡,完全比不上家裡茶餐廳的熱奶茶和菠蘿油。午餐和晚餐也大多是清淡的菜式,讓我時常懷念媳婦煮的住家飯。
最初的幾個星期,我幾乎每天都想回家。院舍的其他長者大多行動不便,交流起來也比較困難。我記得有一次,我試圖和一位同房的長者聊天,但她因為聽力不好,總是答非所問,讓我感到非常沮喪。我更懷念在家裡看電視、讀書的悠閒時光,懷念和孫子一起玩耍的歡樂時刻。
適應新環境的過程充滿了挑戰。我開始嘗試參與院舍的活動,雖然一開始並不感興趣,但漸漸地,我發現這些活動可以打發時間,也能認識一些新朋友。我尤其喜歡每週一次的書法班,這讓我找回了些許生活的樂趣。工作人員也逐漸了解我的喜好,會特別為我準備一些我喜歡的點心,這讓我感到一絲溫暖。
然而,院舍生活也有許多不便之處。最讓我困擾的是缺乏私隱。房間的隔音很差,隔壁的咳嗽聲、談話聲都聽得一清二楚。洗澡和上廁所也需要排隊,有時要等很久。我記得有一次,我因為急著上廁所,等了將近半小時,最後不得不求助工作人員。院舍的醫療服務雖然方便,但醫生每次看診的時間都很短,無法詳細了解我的病情。這些不便讓我時常感到沮喪。
隨著時間的推移,我開始慢慢適應院舍的生活。我學會了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裡安排自己的生活,也學會了如何與其他長者相處。雖然我仍然懷念家裡的自由和舒適,但我明白,老人院的生活也有其優點。這裡有專業的護理人員,可以隨時應對我的健康問題;這裡也有固定的社交活動,讓我不至於完全與社會脫節。
回顧這一年來的院舍生活,我深刻體會到長者從家庭過渡到老人院的艱難。這不僅是生活環境的改變,更是心理和情感上的巨大挑戰。我希望社會能夠更加關注長者的院舍生活,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。比如,增加政府資助的院舍名額,縮短輪候時間;改善院舍的設施和服務,提高長者的生活質量;提供更多的心理輔導和支持,幫助長者更好地適應院舍生活。
作為一個長者,我深知老化是不可避免的過程,但我們仍然希望能夠活得有尊嚴、有質量。希望未來的香港,能夠成為一個真正關愛長者的城市,讓每個長者都能夠在晚年找到屬於自己的安樂窩。這段從家到院舍的旅程,雖然充滿了挑戰,但也讓我學會了如何在新的環境中找到生活的意義。或許,這就是人生給我的最後一堂課:無論身在何處,都要學會適應,學會珍惜,學會在有限的條件下活出最好的自己。